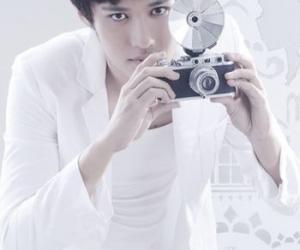随想.外婆
习惯了一个人吃饭、睡觉,习惯了一个人看书、写字,习惯了一个人到处走走,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我总是满足于这样的时光,并且自娱自乐着。于是,习惯了晚睡,安静散乱地思考着一些事。忽然地,就想到了外婆。
外婆的脸早已模糊于时间的荒野,所有关于外婆的记忆只剩下热闹的四合院和沁甜的荷包蛋了。
那时的外婆和几个舅舅舅妈住在一座老旧的四合院,是黄泥垒砌的那种古老的宅子,外婆就住在东面那一通略高的屋子里。每一次母亲回娘家总会带上我,刚进院子外婆就迎了出来,过不了一会儿定会煮上几个荷包蛋。
就是这几个荷包蛋,成就了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我时常在想,要是外婆还在该有多好。然而,外婆终究是离我而去了,来不及我多想,便毅然决然地消失得了无踪影。
今年,我和母亲去看外婆,母亲竟然分辨不出外婆的坟头。印象中,上一次来给外婆扫墓大约是在十多年前。半响,母亲才说,坟前的那只碗像外婆家的。
是啊,十年的时间足够淡忘很多事,包括父母的音容笑貌。母亲说,在她的记忆中,从她明事以来,外婆就是个老太太。但很精神、富态,总是把头发挽成团髻在脑后。
外婆没有上过一天学,却会很多复杂的计算式的问题,会编布。编布是个很麻烦的技术活儿,它需要精确的计算出什么样的布匹需要多少丝线,在怎样的时候通过乱七八糟的工具左穿右插。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仅靠几亩薄田很难养活一家人。然而,外婆家却是个例外。由于外婆编的布整齐耐用,不仅供家用且还能够外卖,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很有点小康家庭的意思。
这些都是听母亲说的。那时幼小的我听得神乎其神,对外婆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然而,在外婆的有生之年,我与她见面的次数几乎只能以个位数计算。唯一能够隐约忆起的画面是最后一次去看外婆。
那年,父母因为生意上的事要远去云南,临走时去看了外婆。贪吃的我再次如愿以偿,外婆给我煮了香甜的荷包蛋。世事变幻无常,谁也不会料到这竟是与外婆的永别。
在云南的日子过的很舒心,因为有永远温润的“春城”。大约是在第四年的一天,母亲突然收到一封信。记得当时母亲拆开信纸,看着看着就红了眼睛,最后干脆哭出声来。我惊愕地看着母亲,母亲说,外婆死了。
外婆就这样走了,在我六岁的时候。之后的第二年父母才带着我回了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外婆。直到这时,我才有机会真正了解一些外婆这几年来的生活。
那个年代的乡下似乎有不成文的规定,儿女成年以后都要“分家”。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也得修两间灶房各自生活。分家以后,老人几乎在转瞬就变成了孩子们的累赘,儿女们都想避而远之。乡下话通常是说父母“跟着谁过”,而不是“该谁赡养”。外婆也是在这样的时候被分家的。
在分家的最初,日子还算平静。随着外公的去世,外婆年事愈高,生活就变得困难起来。外婆隔三差五就生病,舅舅舅妈却聪耳不闻。农村的人们有淳朴的一面,有时候对待老人的态度却令人费解。舅舅舅妈也不例外,总会跟外婆过不去,找机会吵架,恨外婆不能早点死。最后,外婆甚至连自己的灶房也没有了,就在堂屋前的屋檐下搭一个简易灶。姐姐每次给我讲起这件事就对舅妈恨的咬牙切齿,她说舅妈在一个雨天把外婆的锅砸扁扔出了屋子,外婆一天也没吃上饭。
舅妈的吵闹、病痛几乎就是外婆晚年的全部。后来,外婆的视力也完全丧失了,做饭的时候总会被粗糙的柴草刺破了双手。外婆说也好,眼不见为净。终于,在一个温暖的早上,外婆就真的不用看见她不愿看见的了。
姐姐说,外婆死之前吃过安眠药。她曾看见外婆有两个那样的瓶子,年幼的她以为是糖还嚷着说外婆不让她吃,最后在外婆死的时候再次看见,瓶子却已经空了。外婆死得似乎很安详,死的时候她真的在笑,平静地躺在那里,像在熟睡。
我却发现了外婆微笑背后的无奈,总觉得她的人生不应该如此艰辛。我有些后悔,为什么没能与外婆多见几面;为什么外婆在她离世这么多年后才开始在我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事实上,所有关于外婆的片段我只能通过我所知的事实和她留下的记号通过自己的臆想来还原。但有一样东西是不需要我去还原的,它永远那样真实地存在于我记忆深处那个温暖的角落,一如外婆的爱。
那是荷包蛋的清香,外婆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