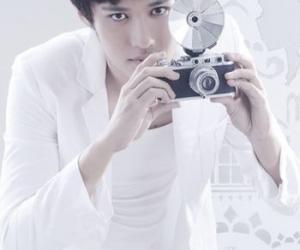我已漠然的心
已经能够坦然走过,马路边乞讨者、卖艺求生者的身边。
已经学会了逃避与伸手向自己乞讨者的目光的交错。
已经开始对捐物、捐款流向的冷嘲,然后漠然。
随着大流质疑着,为什么西部永远是干裂的嘴唇,渴望的眼神,破烂的教室;为什么山区总是佝偻的背影,缠杂的皱纹,一世的沧桑;为什么总是说15岁的年龄,51岁的表情……太多的质疑为自己的冷漠找着借口。一切没有为什么,只因为这些只是他们最原生态的生活状态写照。大部分人已经没有心情去关注他们,大部分人在为蜗居奋斗,在为成功挣扎,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寂寞,在灯红酒绿中孤独,围绕自己身边小小的世界转动,为自己小小的心灵寻找着出口。看完叶楠的纪实小说--把梦留住,开始严重鄙视自己的无病呻吟,大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矫揉造作。他们走两三个小时山路是去上学,他们几十个人以蜷缩的姿态以最小的空间,挤在小小的宿舍,他们一个星期四个馍,他们喝着比海水还难喝的水,冬天零下几十度狂风沙是他们单薄的衣服,看着,想着,谁带他们离开贫困的悬崖。我们在为工作,爱情,寂寞苦恼,他们在为吃饱,喝水,上学挣扎。10多岁,不符合年龄的衣服,不符合年龄的表情,不符合年龄的劳作,不符合年龄的负担。没有依靠,没有贵人,他们像蜗牛只能自己背着壳,背负起自己的家。
人都是有梦想的,只是我们梦想的形状都不一样。如果说:18年的奋斗,农村的我和城市的你才有资格坐在一起喝咖啡。然而,山区的孩子呢,他们是否有一个咖啡的概念,砸锅卖铁读书之势,全家劳作供养一个读书的狠劲,在此时代我想也只有在山区和贫困的地区才能见到了。忽然在脑海里构造阿里的爸爸形象,穿着颜色复杂的粗布的衣服,头上围着杂碎的布条,坐在门口长着青苔的横躺着的树杆上,吸着旱烟,慢慢的吐着烟圈,眼神凝视前方,。似乎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把他压倒,所有的努力必须朝一个方向前进,读书走出大山。放羊―赚钱―盖房―娶媳妇―生崽―放羊,这一个梦想当初看来是这么的好笑,却是许多人世世辈辈的生活写照,他们无力去改变这种现状。读书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希望。
然而,他们的奋斗,等待他们的是和优越条件下成长孩子同等的竞争,读书无用论是不是该把他们最后梦想的一条路堵住。上帝给了世界一个完美的我,我将会还一个怎样的我给上帝?山区人民给了往外面世界如此深刻的渴望,外面的世界又将如何对待这些好奇的精灵?每个人都有梦想,只是我们梦想的形状不一样,我们梦想的轨道不一样,梦想的大小不一样,或许关键在于我们都在为实现梦想的奋斗线上。
支教,西部,走向那里该对生命有多大的热情。那里有最纯正的真善美,也有对生活的无奈与悲伧,对生命渺小的感叹。忍不住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价值欲是什么,是勇攀科学的高峰,是去往最贫瘠的土地,也许只是为自己的生活世界所奔波。我们忙、我们茫、我们盲,我们关心的只是10米以内的事情。原来曾经向往的古代的生活,干净的村落,农间小道,鸡鸣狗吠,男耕女织,只是陶渊明描述中的世外桃源,忘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兵荒马乱,战火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