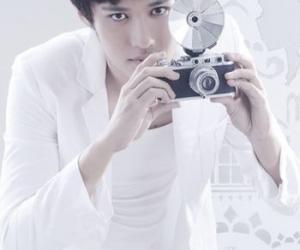记忆中的年糕
作者:suixinsuixing
2011-02-15 09:13
过年了,在我的家乡有吃年糕的习俗。很多地方都有吃年糕的习俗,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吃了年糕,年年高……好吃的年糕,还有美好的意愿。
现在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只要你想,你都可以痛痛快快吃到年糕。但是小的时候,年糕多半是过年过节时才能尽情享受的美味。那时候,小镇街市上大清早时,最多只有一两处卖手工年糕的的摊子。我曾经很多次无比贪恋的看着那一幕:卖年糕的师傅,从遮着白布的米粉团中扯下一块,然后在光滑的木板上用手反复压、揉,把米粉团揉捏成光滑、白嫩的年糕块。接着把年糕块摊开,中间夹入一个香喷喷的油饼,再把年糕团密封起来,笑呵呵地递给一直等在前面的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小孩,那是那个幸福小孩的美味早餐。我一直没有吃过那样的早餐,尽管我无比渴想过。我从来没有向爸妈要求过,因为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不可能吃那种比较豪华的早餐。
过年轧年糕是我们家孩子最欢呼雀跃的时候,(之所以把年糕加工的整个过程称为轧年糕,和家乡的方言有关。)因为那时候爸妈因为家里一帮小孩子几近一年的渴望,加上过年时招待亲戚朋友的需要,所以过年时爸妈总是格外大张旗鼓,很是大手笔的轧它一、二百斤的年糕。轧年糕总是在十二月廿左右就要急急开始准备:那时天气总是很冷的,有时还是阴冷的雨天。打听好有年糕加工的地点后,(印象中轧年糕的地点总是每年都在变化)爸妈要提前一天把准备轧年糕的粳米准备好,把米洗干净,沥水后装箩筐里,再由爸爸挑担箩筐,哥姐抬个箩筐,赶到年糕加工点,排队等待一系列的加工。有时,凑巧那加工点离我们家比较近时,就可以让爸妈先回家忙别的事,我们小孩子就派上大用场了。在加工点守候着,等着轮到加工我们的年糕。绝对不能没人盯着,否则会有别人加塞的。等着、等着,好不容易轮到加工我们家的年糕了:第一个程序是磨粉,先把米舀入一个大漏斗中,在里面米会被磨成米粉,而后从一个被机器排风吹成鼓鼓的布筒子里滑出来,流到箩筐里。然后大人们再把箩筐挑到蒸房,蒸房里排满一个个大大、圆圆的簸箕,把米倒入簸箕内,加工点的人会拿水过来,把米和一和,揉捏揉捏成合适的干湿状态,这是为下一步蒸米粉做准备,两百斤的米粉都和水搓揉完成后,开始一个关键性的程序了,就是蒸米粉。也是我们小孩子最期待的一个环节,因为在年糕米粉被蒸熟后,还未被机器整压成一条条砖块模样的年糕条前,需要倒在刚才的大簸箕中晾凉下,这时候被蒸熟的米粉,我们管它叫糕花,最好吃了。我们兴奋地跟着爸妈在一旁拨拉着糕花,一边拉扯一块块糕花,塞进嘴里嚼着,越嚼越甜,越嚼越香。糕花晾地差不多了,也该轮到我们家的年糕定型了,这是最后一个程序,把蒸熟的糕花拨拉到又一个漏斗筒里,在这里年糕将会被最后压模定型,最后从机器口里掉出来的就是一条条热乎乎的砖块模样的年糕了,有的加工点的模板高级些,压制出来的年糕上面就会有类似“喜字”的吉祥花样。这时小孩子又有了用武之地,年糕条总是掉出来的很块,我们要手忙脚乱的把一条条年糕码到旁边的大簸箕上,不然,那些热乎乎又有些黏糊的年糕会沾粘在一块。码好所有的年糕后,不管是大人和小孩都暂时松了一口气,因为接下来只要等眼前一排排白花花、胖乎乎的年糕稍微晾干些就可以收拾回家了。有好几年都是时间赶得不巧,在漫长的等待、加工后,爸妈把年糕挑或抬回家时,都已经是深夜一两点了。
把年糕挑回家后,还是有一件必做的事。妈妈总是事先腾出一些晾年糕的地方,于是之后较长的时段里:桌上、地板上都是晾满了白花花的年糕。年糕晾好后,还需要经常去翻动,让它们两面都充分晾干。而这当时,年糕在边彻底晾干的过程中,很是有一部份就被晾进了我们的肚子里。过了年,年糕已经充分晾干了,这时不能把剩下的年糕一直还晾到一边,不然,年糕会因为天气发生皲裂或发霉,从而影响口味。于是,爸妈又得准备好一个大大的水缸,把剩下的年糕全部搬到水缸里,再往水缸注入干净的水。这样得以沐浴在清水里的年糕,不仅不会干裂,也不会发霉,但是随着天气的温暖,爸妈还需要隔三差五的更换年糕水。年糕轧的多的年份,我们家的年糕可以一直吃到清明时候,往往在清明的家宴上年糕才得以正式宣布它的使命终结。